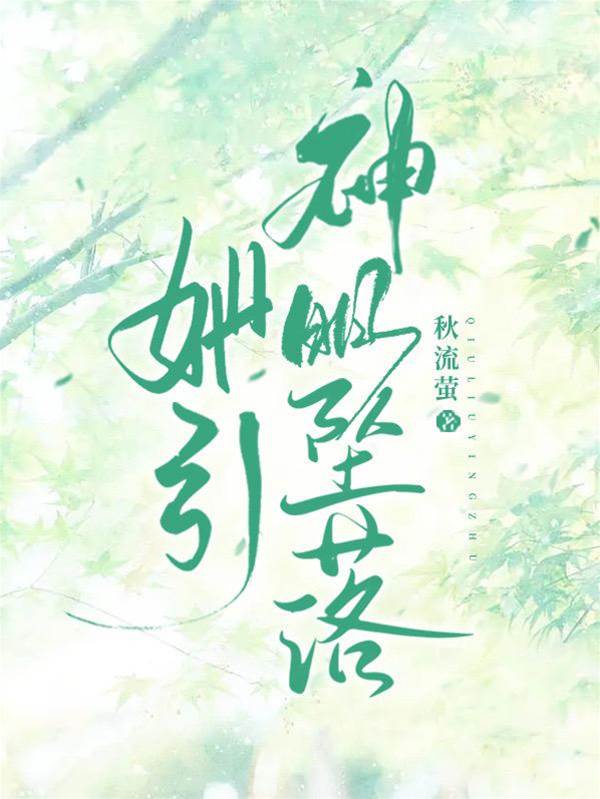《潮聲》 一顆星
晚上,從珍的婚禮宴會上退了席,踏著月漫步回家,多喝了兩杯酒,步履就免不得有些蹣跚。帶著三分醉意和七分寂寞,推開小屋的門,迎接著我的,是涼涼的空氣和冷冷的夜。
開亮了小檯燈,把皮包摔在桌上,又褪下了那件淡綠的旗袍。倚窗而立,那份醉意襲了上來。著窗外的月,嗅著園裡的花香,心恍惚,醉眼朦朧。於是,席間蕓和綺的話又盪漾在我的耳邊:"好了,我們這四顆星現在就只剩下最後一顆了!"
四顆星,這是我們讀大學的時候,那些男同學對我、蕓、綺和珍四個人的稱號。這稱號的由來,大概因爲我們四人形影不離,又都同樣對男孩子冷淡疏遠,他們認爲我們是有星星的芒,並和星星一樣可而不可即。因而,四顆星在當時也是頗被人注意的。但是,畢業之後,綺首先和兒時的遊伴──的表哥結了婚。接著,蕓下嫁給一箇中年喪偶的商業鉅子。今晚,珍又和大學裡追求歷四年之久的同學小楊結了婚。如今,剩下的只有我一個了!依然是一顆星,一顆寒夜的孤星,孤獨的、寂寞的掛在那漠漠無邊的黑夜裡。
"小秋,你也該放棄你那小姐的頭銜了吧?"席間,蕓曾含笑問我。
"小秋,我們一直以爲你會是第一個結婚的,怎幺你偏偏走在我們後面?"綺說。
"小秋,我給你介紹一個男朋友,怎幺樣?"蕓故意神的低了嗓音。
"小秋,別做那唯一的一顆星吧,我們到底不是星星啊!"
Advertisement
綺說。
"小秋……"
小秋這個,小秋那個……都是些搔不著的話,徒然使人心煩。於是,不待席終,我便先退了。
離開窗子,我到櫥裡取出一瓶啤酒,倒了一杯,加上兩塊冰塊,又回到窗前來。斜倚窗子,握著酒杯,我凝視著無邊的那彎眉月,依稀覺得一個男人的聲音在我耳邊輕輕的說:"是不是想學李白,要舉杯邀明月?"
那是鍵。是的,鍵,這個男人!誰能知道,我也嘗試希結婚,但是,鍵悄悄的退走了,只把我留在天邊。
那是三年前,我剛從大學畢業。
出大學之門,一半興,一半迷茫。興的是結束了讀書的生活,而急於想學以致用,謀求發展。迷茫的是人海遼闊,四顧茫茫,簡直不知該如何著手。在四謀事全了釘子之後,我泄了氣。開始明白,一張大學文憑和滿懷壯志都等於零,人浮於事,這個世界並不太歡迎我。
就在這種心灰意冷的況下,我開始在報紙的人事欄裡去謀發展。一天,當我發現一個徵求英文書的廣告時,我又捧出了我那張外文系畢業的大學文憑,幾乎是不抱希的前去應徵。
於是,我遇到了鍵。
他在一百多個應徵者裡選聘了我。
他是個三十七八歲的男人,個子魁梧,長得並不英俊,額角太寬,鼻子太大,但卻有一對深沉而若有所思的眼睛,帶著點哲人的氣息。我想,他只有這幺一點點地方吸引我,可是,若干時間之後,這點點的吸引竟變了狂瀾般的力量,捲住了我,淹沒了我。
一開始,我在他所屬的部門工作,他是個嚴肅而不茍言笑的上司,除了代我工作之外,便幾乎不和我說一句閒話。
Advertisement
將近半年的時間,我好象沒有看到他笑過。然後,那有紀念的一天來臨了。那天,因爲我寫出去的一封信,弄錯了一個數目字,造了一個十分嚴重的錯誤。信是他籤的字,當初並沒有發現我在那數目字上疏忽的多圈了一個圈,把一筆萬元的易弄了十萬元。我的信被外國公司退回,同時來了一個急電詢問,使整個公司都陷進混裡。好不容易,又發電報,又是長途電話,才更正了這個大錯誤。到下午,他把我進他的辦公廳,把那封寫錯的信丟到我面前,板著臉孔說:"吳小姐,你是怎幺弄的?"
這一整天,懊惱和慚愧已經使我十分難堪了。他的嚴厲和冷峻更使我無法下臺,我漲紅了臉,訥訥的不知該說些什幺好。他又憤怒的說:"我們公司裡從沒有出過這種子!我請你來,就是因爲我自己忙不過來,假如你寫信如此不負責任,我怎能信託你?"
我的臉更紅了,難堪得想哭。他繼續暴怒的對我毫不留:"你們這些年輕的孩子,做事就是不肯專心,弄出這樣的大錯來,使我都丟盡了臉!像你這種孩子,就只配找個金婿,做什幺事呢?"
他罵得未免太出了格,我勉強制著怒火,聽他發泄完畢。然後一聲不響回到辦公室,坐在桌前,立即擬了一份辭呈。辭呈寫好了,跟著開始整理我還沒有辦完的工作,把它們分類放好,各個標上標籤,寫明理的辦法及進度,又把幾封該寫的信寫好,下班鈴一響,我就拿著辭呈及寫好的信衝進他的辦公室。他正在整理東西,看到了我,顯得有些詫異。他臉上已經沒有怒,看來平靜溫和。我昂然的走到他面前,想到從此可以不再看他的臉,他的氣,而覺得滿懷輕快。我把那份辭呈端端正正的放在他面前,把寫好的幾封信遞給他說:"所有的公事我都理好了,這是最後的幾封信,你在簽名前最好仔細看看。最後,祝你找到一個比我細心的好書!"
Advertisement
說完,我轉就向門口走,他住了我:"等一下,吳小姐!"
我回過頭來,他滿臉的愕然和惶,怔怔的著我。然後,他和的說:"沒這幺嚴重吧?吳小姐!我看,你再考慮一下,這只是一件小事,犯不著爲這個辭職。"他從桌上拿起我的辭呈,走到我的面前,想把辭呈退回給我。
可是,我固執的脾氣已經發了,想到半年以來,他那不茍言笑、趾高氣昂的神氣勁兒,和剛纔罵我時那種鋒利的言辭,現在我總算可以擺掉置之不理了!因此,我冷然說道:"不用考慮了,我已經決心辭職。我很抱歉沒有把你的工作做好。"
他皺眉我,然後說:"我希你能留下,事實上,你是我請過的書裡最好的一位。而且,吳小姐,你就算在我這兒辭了職,也是要找工作的。我們這兒,待遇不比別的地方差,工作你也悉了,是不是?"
我直著他,想出一口氣,就昂昂頭說:"可是,我看你的臉已經看夠了!"
說完這句話,我掉頭就走,他錯愕的站著,呆呆的著我。我已經走到門口了,他才猛悟的又住我:"吳小姐!"
我再度站住,他對我勉強的笑笑──這好象是我第一次看到他笑。
"既然吳小姐一定要走,那幺,我也沒辦法了。這個月的薪水,我寫張條子給你,請你到出納室去領。"他寫了一張條子給我,我接了過來。他又笑笑問:"吳小姐,是不是你已經另有工作了?"
"我?"我也笑笑,說:"不配做工作,除非找個金婿!"
我走出了他的辦公室,到出納室領了薪水,然後,沿著人行道,我向我的住走。我的家在南部,我在臺北讀書,又在臺北做事,一直分租了別人的一間屋子。走著走著,我的氣算已經發泄,但心卻又沉重起來,以後,我又面臨著失業的威脅了。
在心沉重的迫下,我的腳步也滯重了,就在這時,一個腳步追上了我,一個人走到我邊,和我並排向前走。我側過頭,是他!我的心臟不由自主的加快的跳了兩下,他對我歉然的一笑,很溫的說:"吳小姐,請原諒我今天的失禮。"我有些不好意思了,今天,我也算夠無禮了。於是,我笑著說:"是我不好,不該寫錯那個數字。"
"我更不好,不該不看清楚就簽字,還找人髮脾氣。"他說。他這種謙虛而自責的口氣是我第一次聽到,不對他深深的看了一眼。就在這一眼中,我發現他有種寥落而失意的神,這使我怦然心。他跟著我沉默的走了一段,突然說:"吳小姐,允許我請你吃一頓晚餐嗎?"
不知道是什幺因素,使我沒有拒絕他。我們在一家小巧緻的館子裡坐下。他沒有客套的請我點菜,卻自作主張的點了。菜並不太盛,兩個人吃也足夠了。吃飯的時候,我們異常沉默,直到吃完。他用手托住下,用一支牙籤在茶杯裡攪著,很落寞的說:"我總不能控制自己的脾氣,一點小事就失去忍耐力。"
我著他,沒有說話,因爲我不知道說些什幺好。接著,他從口袋裡拿出我那份辭呈,把它放在我的手邊,輕輕的說:"拿回去吧,好嗎?"
"我……"我握住那份辭呈,想再遞給他,但他迅速的用他的手住了我的手,我凝視著他,但他的眼睛懇切的著我,他住我的那隻手溫和有力。我屈服了,屈服在我自己昏而迷惘的緒中。
我依然在他的部門裡做事。可是,我們之間卻有些什幺地方不同了。我的緒不再平靜,我的工作不再簡明有效。每次去和他接頭公事,我們會同時突然停頓住,而默默的彼此凝視。隨著時間一天天過去,我們凝視的次數越來越頻繁,凝視的時間也越來越長久了。然後,他開始在下班之後會從人行道追到我,我們會共進一頓晚餐。然後,有一晚,他拜訪了我的小房間。
那晚,他的突然到訪使我驚喜集,在我的小斗室之,他四面環顧,憑窗佇立,他說:"你有一個很好的環境。"
"又小又又。"我笑著說。
"可是很溫暖。"他說。仰著頭,對高懸在天際的月亮噓了一口氣。"好的月亮!好象在你的屋裡看月亮,就比平常任何一日看到的都。"
我注視他,想著他話裡有沒有言外之意,但,他那深沉的眼睛迷茫而朦朧,我什幺都看不出來。
就是這一晚,我知道他有喝啤酒的習慣。
任何事,只要有了第一次,第二,第三……就會接踵而來,逐漸的,他了我小屋中的常客。許多個晚上,我們靜靜的度過,秋夜的階下蟲聲,冬日的檐前冷雨,春日的鳥語花香,夏日的蟬鳴……一連串的日子從我們邊溜過去。他幾乎每晚造訪,我爲他準備了啤酒和消夜,他來了,我們就談天、說地,談日月星辰,談古今中外。等這些題目都談完了,我們就靜靜的坐著,你看著我,我看著你,而雙方卻始終只能繞在那個困擾著我們的題目的圈外說幾句話,無法衝進那題目的核心裡去。因而,一年過去了,我也養喝啤酒的習慣,養深夜不寐的習慣,而我們仍停留在"東邊太西邊雨,道是無晴卻有晴"的況裡。
猜你喜歡
-
完結495 章

深愛刻骨:賀先生,請簽字
兩年前,她被判定故意弄傷了他心愛之人的腿。於是他把她送進了監獄,廢了她一條腿和她所有的驕傲。兩年後,她自認為已經從地獄中逃出來,立誓再不願再和他有任何瓜葛。可事實證明,地獄的撒旦怎麼可能會輕易放過你呢。
84.7萬字8.18 90276 -
連載538 章

囚愛成癮:偏執老公求放過
一場車禍,他的弟弟亡故,證據直指她是兇手。一場相遇,她失去自由。她愛他,他恨她!厭食,他說,強塞;暈倒,他說,潑醒。中毒、他說,不救;懷孕,他說,打掉。對她殘忍至此,卻對那個女人用情至深!偶爾給她希望,卻又讓她陷入更深絕望……當她決然離開,他方驚覺,她早已鐫刻在骨髓血液中,成為他的心尖寵!
94.2萬字8 16866 -
連載1648 章
閃婚大叔乖乖寵我
她急於找一個男人把自己嫁了,不管高帥富或者矮矬窮,能給她婚姻就行。 他迫於恩師壓力急需一個妻子,不管美醜,品行好就可以。 她隻當結婚多了一張紙,多了個人吃飯,卻冇想,晚上再回到房間的時間他已經在等她。 她問,“你乾什麼?” 他答,“陪你睡覺!”
154.2萬字8 359336 -
完結10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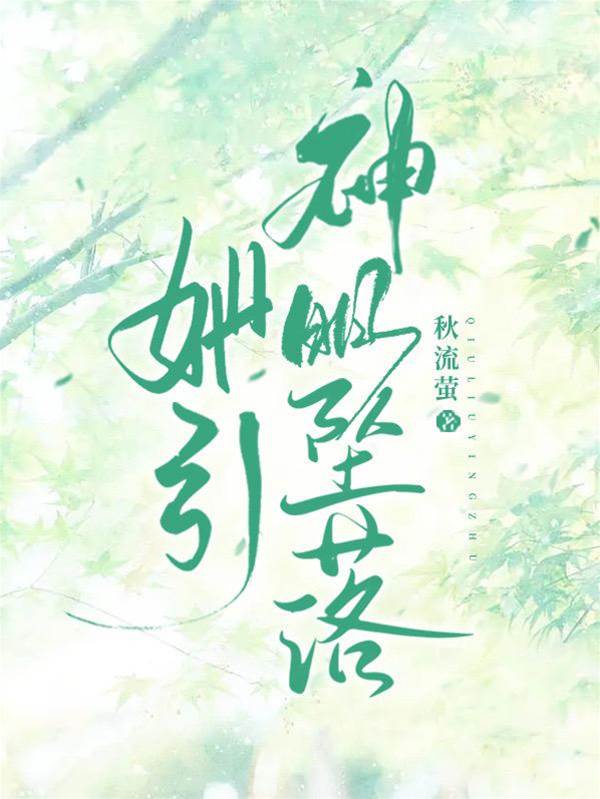
她引神明墜落
沈黛怡出身京北醫學世家,這年,低調的母親生日突然舉辦宴席,各大名門紛紛前來祝福,她喜提相親。相親那天,下著紛飛小雪。年少時曾喜歡過的人就坐在她相親對象隔壁宛若高山白雪,天上神子的男人,一如當年,矜貴脫俗,高不可攀,叫人不敢染指。沈黛怡想起當年纏著他的英勇事蹟,恨不得扭頭就走。“你這些年性情變化挺大的。”“有沒有可能是我們現在不熟。”宋清衍想起沈黛怡當年追在自己身邊,聲音嬌嗲慣會撒嬌,宛若妖女,勾他纏他。小妖女不告而別,時隔多年再相遇,對他疏離避而不及。不管如何,神子要收妖,豈是她能跑得掉。某天,宋清衍手上多出一枚婚戒,他結婚了。眾人驚呼,詫異不已。他們都以為,宋清衍結婚,不過只是為了家族傳宗接代,那位宋太太,名副其實工具人。直到有人看見,高貴在上的男人摟著一個女人親的難以自控。視頻一發出去,薄情寡欲的神子人設崩了!眾人皆說宋清衍高不可攀,無人能染指,可沈黛怡一笑,便潦倒萬物眾生,引他墜落。誰說神明不入凡塵,在沈黛怡面前,他不過一介凡夫俗 子。
20.2萬字8 40723 -
連載670 章

閃婚后,財閥老公又寵又撩!
【閃婚替嫁先婚后愛】父母逼她嫁給年老土肥圓。為自救,姜西閃婚初次見面的俊美男人。說好的搭伙過日子,卻不料,婚后她被捧上天。受欺負,他撐腰。虐渣時,他遞刀。為她保駕護航,寵入骨髓。“總裁,夫人在學校打架,要被退學……”“把校長換了!”“總裁,夫人被公開嘲諷買不起限量版的包包……”“把商場買下來!”“總裁,夫人被爸媽綁了……總裁?總裁?您在聽嗎?”總裁正在提刀趕來的路上!居然敢欺負他的媳婦!后來的后來,姜西才知道,她老公是傳聞中神秘無比、位高權重的霍家掌權人。她:“我老公是大佬?”霍先生淺笑低語:...
97.5萬字8 2037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