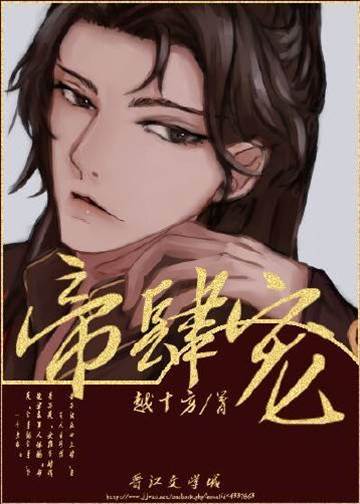《錯嫁皇妃帝宮沉浮:妃》 第十章
,難道真的喜歡那個男子,不因為份,不因為其他嗎?
或許,不過是年的一種執念,總以為,那人是該去喜歡的,那人的份,那人的神,都只化作時的執念。
所以,用各種方法去贏得他的注意力,哪怕,帶著對彼此的傷害,都要那一人注意到自己。
可,未必是喜歡,即便到了現在,不愿意由他來發落,不過,是出于對心底,那份執念的維護。
僅是這樣,罷了。
許是坐的太久,突然起,說完這句話,的腳一麻,子就往夕上倒去。
夕扶著,撤手不及,眼前要到跌下去。
一只有力的手說時遲,那時快擋住夕搖搖墜的后背,能覺到,手心的暖融,著不算薄的披肩,一并融了進來。
記憶里,那人的手心,總是冰冷的。
一如,現在的手心一樣。
為什麼,又想起他呢?
閉上眼睛,睜開的剎那,看到伊泠的眼里有著煙火閃現,不過一瞬,恢復清冷:
“風長老。”
伊泠喚出這三字,怯怯地掙開夕扶住的手,繼續道:
“風長老,我不是有意的,我不是——”
“回去吧。”風長老的聲音在吸煙的耳邊響起,復對伊泠,“一個人,若自己都不惜自己,那麼,沒有人會比自己更惜。”
這句話聽上去很冷冽,實際,卻是對的。
自己的,惟有自己去懂得惜。
伊泠似乎說了一句什麼,又似乎,不過是的囁嚅。
,真的喜歡的,僅是風長老的份嗎?
的手拽著夕的帕,著風長老扶著夕離去的背影,心里郁堵的地方,終是嗆出了一種悲傷。
回,出殿的剎那,夕問了風長老一句話:
Advertisement
“明日,你準備怎麼發落?”
“謀逆之罪,最當誅,留下的命,已是最大的限度。”
“不過是了人唆使,若要追究,幕后的人,焉能幸免?”夕說出這句話,眸華若有似無地瞥了他一眼,復道,“就把發落到偏遠的部落去吧。是伊氏的庶系,我不希,伊氏的人,在拘謹里過完這一輩子。”
風長老知道,夕這一睨的意思,除了沉聲應允外,他沒有做任何的反對。
此刻,不知道,是不是夜深了,一陣風吹過,夕突然覺到,的子一陣的發冷,這種冷,似乎不全是從外沁,而是從心里蔓延出來,一點一點的,滲進里,然后帶到全的,讓每一,都冰冷起來。
下意識地了子,加快步子往金凰殿走去。
心地泛起不祥的預兆——
這,難道就是毒發麼?
不要讓人看到的弱,尤其是風長老,否則,他一定不會容許保下腹中的孩子。
越走越快,風長老形微,卻是阻到的面前:
“你要去哪?”
“回殿。我累了。”說出這五個字,竭力克制住字里的音。
“這里不是回金凰殿的路,那邊才是。”風長老手指回廊的另外一。
是了,本對王庭不悉,竟然,妄想著自己能走回去。
“恩,我讓侍衛帶路,你也早點歇息吧。”
這句話太長,的聲音里,明顯帶了無法遏制的音。
“你怎麼了?”風長老說出這句話,再不顧避嫌地執起的手,的手冰冷一片。
的眉心也凝了點點的霜寒。
“夕——”他喚出這一個字,不顧這邊上的侍衛在場,打橫抱起,迅速奔向金凰殿。
Advertisement
而夕連推開的力氣都仿佛被凝結了冰。
四肢一片僵,之下意識地想要汲取一點溫暖。
一點點都好啊。
然,他的溫暖,是不能汲取的。
僵著姿勢,只讓自己陷更深的寒冷中。
風長老幾乎是狂奔回金凰殿,甫進殿門,就命令阿蘭:
“速把冰盆撤掉,換上碳盆!”
“碳盆?”
阿蘭稍稍遲疑一下,立刻明白過來,忙吩咐殿外的婢去做。
在轉時,看到,風長老抱著夕的影已消失在殿。
他從來不抱人的。
無論什麼時候,他都不愿意抱人。
為什麼,這一次又破例了呢?
阿蘭別過臉,不再去向殿。
冰盆撤去,碳盆攏上時,突然覺得自己的心,其實并不比盆里的溫度高多好。
任碳盆再如何攏了碳,都溫暖不了的寒冷。
惟有,他的溫能溫暖。
可惜,有多久,沒有覺到他的溫了呢?
不能繼續想下去,不然,真的做不到淡然。
待使婢放上火盆,掩上殿門,退了出去。
殿外殘月如鉤,一如的心境,原來,了他,便殘缺不全了。
上一個男子,注定是人最大的劫數。
只有不,才不會傷。
仰起臉,著那殘月,輝映出過往和他的點滴。
夕俯下子,的手抓著榻上的褥子,卻毫不能環節上的寒冷。
好像,整個人快變冰一樣,牙齒不停地打這種戰,全,都漸漸不再的控制。
不知道死的滋味,但,想,或許,現在的滋味,不必死好得了多。
是的,死,至一了百了。
那絕不是單單的寒冷所能詮釋的覺,是每一次的呼吸,都會被凍結到宛如尖刀,割進心里的滋味。
Advertisement
的子蜷一團,然,這樣,不過是徒勞的。
驀地,有一床稍厚的棉被裹住的,接著,他的聲音在他的耳邊響起:
“別咬到舌。”
是的,牙齒這麼打戰,萬一咬到舌,那真的就是自盡了。
習武者,牙齒再怎樣打戰,都能控制住,避開舌的要,而,不懂任何武藝,所以,只能用力咬住褥子,去控制咬到舌,可,很快,褥子就被咬得對穿。
或許,下一個瞬間,就或咬到舌。
原來,他的意志力始終還是薄弱的。
開始去尋找下一個可以咬的東西,而他的手,終于從后面擁住的子,即便隔著不算薄的棉被,能覺到他的溫暖,一層一層的傳遞給。
可不夠啊,需要更多的溫暖,需要。
然,怎能要他的溫暖呢?
“別——”他的聲音低低的,在耳邊響起。
就這兩個字,突然,讓有悉的覺。
是這兩個字悉,還是他的聲音悉呢?
這份悉,讓的突然放棄了拒絕。
好像,抱著他的,是那一人。
只是,那一人。
眼睛被冰霜凍得僵麻地睜不開,索著被上的棉被,然后,把它拉下,突然,咬到了很的東西,不象褥子那般讓只咬得要吃發冷。
很,還很溫暖。
這些溫暖順著的齒間,慢慢地溢進去,溢進去。
的齒,稍稍好了許多,想睜開眼睛,看看那東西,可,眼簾真的好難掙開。
上的冷,和著現在齒的溫暖,的第一次毒發,終于,就這樣昏昏沉沉地熬了過去……
耳邊,傳來清脆悅耳的鳥聲時,才緩緩醒來。
上的冷意早被驅散,躺在溫暖的被子里,捂出了一干燥的汗意。
Advertisement
瞧了一下,原來,昨晚擁住的棉被,不知何時,換了薄毯,倘若還是錦被,估計配上現在殿的溫度,那就不僅僅是出汗這般簡單了。
殿,似乎只有他一人,挪了一下子,想要坐起來。卻發現酸疼得。
不過,終于,熬過來了,不是嗎?
昨晚依稀的印象里,似乎,風長老一直抱著,哪怕隔著一層被子,那份覺是清晰的。
而彼時的呢?
不愿繼續回想,承認,那一瞬間,是懦的。
這份懦,真的僅僅因為毒發的寒冷,還是,把他當了誰呢?
不,不能再想!
環顧了一下四周,映眼簾的,卻是蹦跳而至的阿蘭。
阿蘭烏黑的眼珠子蘊著濃濃的笑意,道:
“族長你醒了?”
“恩,昨晚——”夕猶豫一下,阿蘭卻已接口道:
“昨晚風長老送族長回來的,他說您累了,讓我們不到辰時不要打擾你。”
“哦。”
正在此時,殿外,清晨驕的輝里,走來青的影,阿蘭側了一下臉,語音歡快:
“風長老。”
“你先下去,替族長準備早飯。”
“好啊。”阿蘭起,瞇眼笑地走了出去。
風長老在夕跟前坐下,他的手端著一碗湯藥,遞給,道:
“喝了它吧,你不喝藥,不僅對你上的毒沒有好,對你的胎兒也沒有任何好。”
“你答應了?”低低問出這句話。
“是,我會盡我所能幫你保住孩子,但,你也要答應我,每日按時喝我給你的藥。”
這個子用倒掉不喝的方式來等他給出這句承諾,那麼,現在他給了。
既然是要的,或許,這是他能給做的不多幾件事之一。
夕的手接過那碗藥,黑褐的藥湯,冒出些許的白氣,能覺到碗壁的溫熱,這份溫熱,其實是一直要的。
湊近藥碗時,凝了他一眼,縱然,只看得到那張面,除此之外,再看不到任何多一點的東西,還是把這碗藥一飲而盡。
不相信任何人。
只相信,哪怕眼前的人不純粹,可,卻不會再這個時候,做出讓與他反目的事。
他想要什麼,如果猜得沒錯,已經知道。
很快把藥喝完,他遞來一小碟餞,淡淡地笑道:
“不用了,反正吃不出味道來。”
他有些訕訕地收回去,略側了臉,道:
“明日是族長的加冕儀式,儀式后,你就是苗水族的族長。”
“恩,苗水族再次出現的那日,應該,這里,就會引來夜國的兵隊吧。”夕執起帕,輕拭上的藥漬。
是的,蚩善加強了排查,雖不會有士兵混疆寧,但定有夜國的細作冒充三國邊境返回的族民混了進來,而這些細作除了探聽這些消息外,最大的功效,怕就是兩軍對壘時,起到煽民心的作用。
這,才是最可怕的。
但,,不愿意苗水的百姓在遭到二十年前的生靈涂炭。
所以,想,知道該怎麼做了。
然,風長老悠緩啟的話語,將的思路打斷:
“夜國至目前還按兵不,可,巽國的兵隊已到斟國的邊境,開戰是迫在眉睫了。”
“風長老還是擔心,一旦斟國被巽國所滅,那麼,于我們苗水族必是亡齒寒?”夕放下手里拭的帕,看似漫不經心的道:“風長老,巽帝的檄文是否是屬實的?我們這次能攻進旋龍谷,若非其中一國相助,按道理,不該這樣順利進到鹿鳴臺,即使,三國帝君只帶一萬的兵,可,駐守在旋龍谷的護軍,遠不止這個數啊。”
風長老沒有立刻回答這句話,他面后的神仿佛是探究,又仿佛是在思忖該如何回答才是最妥帖的。
不過須臾,他思緒甫定,再次啟,卻是承認的:
“是,我們苗水族確實與斟國有過協定。”
沒有繼續問為什麼以斟國之尊,愿意和苗水合作,難道,僅僅是因為夜、巽兩國好,斟帝借挑撥夜、巽兩帝失敗,才急于找一個聯盟嗎?
但,目前表面來看,就這麼簡單。
那麼,且相信,就這麼簡單吧。
“我明白了。”說出個句話,并不再多言。
但,風長老仍是說出了下一句話:
“族長,你的孕目前雖只有一個月,不過,很快就會顯形,屆時,你仍是需要給族民一個代。”
猜你喜歡
-
完結2476 章
一世傾城:冷宮棄妃
那一夜,她褪去了少女的青澀,成為冷宮深處的悲傷漣漪...... 那一天,她跪在他的腳下苦苦哀求,她什麼都不要,只想要出宮,做個平凡女人... 幾個風神俊秀的天家皇子,一個心如止水的卑微宮女... 當他們遇上她,是一場金風玉露的相逢,還是一闕山河動蕩的哀歌......
600.3萬字7.82 720803 -
完結392 章

庶女嫡妻:將軍請自重
上一世,駱銘忠君愛國,卻英年早逝,死無全尸;夏芷瑜孝順嫡母,卻終身無子,死于非命。這一世,‘不孝有三,無后為大’四個字,意外地將前世毫無交集的兩人牽扯到了一處。 夏芷瑜“我和他青梅竹馬,但終究緣分不夠深,他只留了個孩子給我,就……”‘詐尸’的駱銘“……”他是孩子爹,但并不是她的竹馬,也沒有咽氣。
89.5萬字8 42959 -
完結8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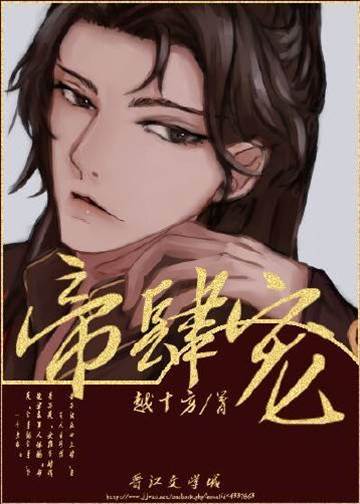
帝肆寵(臣妻)
從軍六年渺無音訊的夫君霍岐突然回來了,還從無名小卒一躍成為戰功赫赫的開國將軍。姜肆以為自己終于苦盡甘來,帶著孩子隨他入京。到了京城才知道,將軍府上已有一位將軍夫人。將軍夫人溫良淑婉,戰場上救了霍岐一命,還是當今尚書府的千金,與現在的霍岐正當…
28.8萬字8 24873 -
完結470 章

重生后太子妃黑化了
身為威遠侯府嫡長女又被選為太子妃的清舒以為自己註定幸福! 她驕傲得如同一團火焰! 太子不喜無所謂,只要做好太子妃就好。 所有人也都這樣告訴她。 直到回到娘家被娘家算計,落得名聲盡失,再也不配為太子妃,成為棄婦送到山上纏綿病榻死了一次蘇醒了前兩世記憶才知道一切都是陰謀! 有著前世記憶又在現代活了一世的她決定這太子妃不當了! 要當就當皇后,當太子他娘! 天下沒有誘惑不了的男人! 女人的身段,臉都是籌碼。 她扭著腰枝走向高高在上的九五至親尊,嫵媚一笑望著手握天下的皇帝。 所有人都說前太子妃一介棄婦,要名聲沒名聲,要什麼沒什麼,就該好好去死,成全大家。 可恨竟然敢誘惑皇上,不要臉,不知廉恥,這樣的女人誰要?皇上那麼英明神武,潔身自好,哪會要這樣的女人! 都等著看笑話。 讓人大跌眼鏡的是他們英明神武的皇上最後居然要了這個狐媚子不說,後來更是帶入宮。 寵在懷裡,疼在骨子裡,可以說含著都怕化了。 簡直是一代妖妃! 大家到此只能等她去死。 據說這狐媚子弱柳扶風,就是一個藥罐子。 可惜等來等去,只等到這個狐媚子生子再生子,還活得好好的,氣死個人!
118.1萬字8 22423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