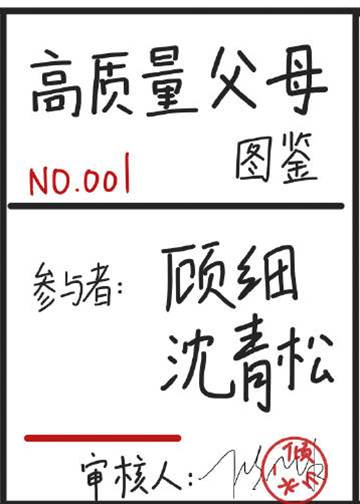《煙雨濛濛》 CHAPTER 12
我站在如萍的房門口,慄地著門裡的景象,如萍的子展地躺在牀前的地下,服是整齊的,穿著一件綠紗白點的洋裝,腳上還穿著白的高跟鞋。向來不長於打扮,但這次卻裝飾得十分雅緻自然。手槍掉在的邊,子彈大概從的右太穿進去,頭頂穿出來,的頭側著,傷口流出的並不太多,一綹頭髮被浸,在傷口上。我著的臉,這張臉——在昨天,還那樣活生生的,那張閉的和我說過話,那對眼睛曾含淚凝視過我和書桓。而今,不害地躺在那兒,任人蔘觀,任人審視,臉是慘白的,染著污,眼睛半睜著……據說,死的人若有不甘心的事,就不會瞑目的。那麼,是不甘心的了?想想看,才二十四歲,二十四,多好的年齡,但竟放棄了的生命!爲什麼這樣做?我知道原因,我知道得太清楚,清楚得使我不敢面對這原因——並不是自殺,應該說是我殺了!著那張臉,我依稀看到昨天的淚眼,那樣無助,那樣悽惶,那樣充滿了無盡的哀傷和絕……我閉上眼睛,轉過子,踉蹌地離開這房門口,我撞到何書桓的上,他站在那兒像一尊石膏像,我從他邊經過,搖晃地走進客廳裡,倒進沙發椅子中。我頭腦昏沉,四肢乏力,如萍污的臉使我五臟翻騰嘔。一個人拿了杯開水給我,我擡起頭,是昨天問過我話的警員,他對我安靜地笑笑說:
“許多人都不能見到死。”
我抖著接過那杯水,一仰而盡。那警員仍然平靜地著我說:“真沒想到,你家裡竟接二連三地出事。”
Advertisement
“我實在沒想到,”我困難地說,“咋天還好好的!”
“我們已經調査過了,證明是自殺,只是我們有幾個疑點,你爸爸的手槍怎麼會到手裡去?”警員問。
“我……”我蹙眉頭,我知道得太清楚了,那是我給的,爲了避免爸爸用它行兇,我怎能料到,如萍竟用它來結束了的生命!只要我預先料得到這種可能的百分之一,我也不會把槍給的。我搖搖頭,艱地說:“我不知道。”
“你知道你父親平日放槍的地方嗎?”
“我不知道。”
“你能不能提供一點你姐姐自殺的原因?”
“我……”我囁嚅著,又搖了搖頭,“我不知道!”然後我鼓著勇氣問:“沒有留下書?”
“只有這一張紙,在桌上發現的。”
那警員打開記事本,拿出一張紙條給我看,紙條確實是如萍的筆跡,潦草地寫著:
我厭倦了生命,所以我結束我自己,我的死,與任何人無關!
陸如萍×月×日
我把紙條還給警員,警員又問:
“據下說,今天早上,令姐還出了一趟門,回來之後就自殺了,到哪裡去的嗎?”
“我不知道!”
警員點點頭走開了。於是,我纔看到爸爸像泥塑木雕一樣坐在一張沙發裡,咬著他的菸斗,而菸斗中星火俱無。我站起來,踉蹌地衝到他邊,和他並坐在一起,我用手抓住他的手,他的手是冰冷而抖索的,我說:
“爸爸!哦,爸爸!”
爸爸不響,也不,依然直地坐在那裡。我到上一陣發冷,爸爸的神更加驚嚇了我。他目呆滯,角上,有一條白的口涎流了下來,沾在他花白的鬍子上。我搖搖他,又喊:
Advertisement
“爸爸!”
他依然不,我拼命搖他,他纔回過頭來,了我一眼,低低地說:
“死了——就這樣死了——只有一槍!放槍的技和我一樣好!”他搖著他的頭,好像他的頭是個撥浪鼓。同時,他把他的手開,枯瘦的手指平放在他的膝上,他凝視著自己的手,喃喃地說:“陸家的槍打別人!不打自己!”他的菸斗落到地上去了,他沒有去管它,繼續說,“這手槍跟了我幾十年,我用它殺過數不清的生命!”他把手抖地到我的眼前來,使我恐懼,他低聲音說:“我手上的污太多了,你不知道有多生命喪失在這雙手底下……所以,如萍也該死在這槍下,帶著我的污去死!”
我抖,恐怖震懾了我,爸爸是頂強的,他不是個宿命論者,他從不相信天、上帝和命運,他只相信他自己,我也一樣。但,他竟被命運折服了嗎?他也認爲他自己是個罪人了嗎?
門口有一陣,來了一個高大的人,提著口醫生用的手提箱,我知道這是法醫。我坐在客廳中等待著,爸爸又閉著不說話了。一會兒,法醫走了。先前那個警走過來,對我說:
“一切沒問題了,你們可以爲安排下葬了。”
警員們和法醫都走了之後,室突然變得可怕地空曠和寂寞起來。阿蘭不知道跑到哪裡去了。四周寂靜如死。我和爸爸都呆愣愣地坐著,誰也無法開口。好半天,何書桓從走廊裡不穩地走了進來,他徑直走到茶幾旁邊,在煙盒裡取出一支菸,我知道他是不菸的,這只是他想鎮定自己而已,他坐進沙發裡,燃著了煙,猛了一口,他並沒有嗆咳,只是臉蒼白得很。就這樣,我們三人坐在客廳中,各人想著各人的,沉默得一如空氣都凝住了。而後面屋裡,一正橫陳著。
Advertisement
何書桓的那支菸完了,菸燒了他的手,他拋下菸,突然站起來說:
“我去打電話給殯儀館!”
爸爸看了他一眼,沒有說話,我也一語不發。於是何書桓走出了大門。沒一會兒,他打完電話回來了,又落坐在原來的位子上,出手再取了一支菸。我著那一縷青煙,在室嫋嫋升騰,再緩緩擴散,心中空虛得如一無所有。咬了脣,我希我能痛哭一場,可是我的嚨口堵塞著,什麼聲音都發不出來。
殯儀館的人來了,一切仰仗何書桓照應,我和爸爸都癱瘓在沙發中,一也不。沒多久,他們把如萍用擔架擡了出來,上蒙了一塊白布。我慄了一下,不由自主地站起來,跟著擔架衝到大門口。何書桓扶著門站在那兒,著擔架被擡上車子,他低低地,自言自語地說:
“一個善良而無辜的孩。”他搖搖頭,嚨哽塞地吐出四個字:“死得冤枉!”
我靠著門,心中惶無所據,一種不願相信這是事實的緒抓住了我,或者我會在下一分鐘醒過來,發現自己正躺在牀上,這一切不過是個荒誕無稽的噩夢。這一定不會是事實,一定不會!何書桓看了我一眼,說:
“殯儀館的事給我吧,你去照顧你父親。”他著那輛殯儀館的黑車子,臉上浮起一個比哭還難看的慘笑,眼睛裡涌上一淚水,幽幽地說:“我昨天才對說過,希我能爲做一點事——沒想到,今天竟由我來護送到殯儀館,我爲做的事,居然是的人生所該做的最後一件。”
何書桓上了殯儀館的車子,跟著車子走了。我著那車子所捲起的塵土,好半天,都不知之所在,模模糊糊地,我竟莫名其妙地想起基督徒葬禮時用的禱辭:
塵歸塵、土歸土、灰歸灰。
是的,“塵歸塵,土歸土,灰歸灰。”這就是生命,來自虛無,又返回虛無。二十四年,給這世界留下了些什麼?現在,就這樣一語不發地去了,像塵、像土、像灰!再也不會悲哀了,再也不會爲獲得和失去而傷心難過了。如萍,到底做了件厲害的事,用的死對我和書桓做了最後的無聲的抗議。在活著的時候,從不敢對我正面說什麼……而今,去了!死者已矣,生者何堪?
車子完全看不見了,我回過子來,這纔看到阿蘭正提著個小包楸,站在我後,看到我回頭。扭著子,出一口金牙,咧著皺著眉說:
“小姐,我不做啦,我要回家啦!”
我的思想還在如萍上,瞪著,我本不明白的意思,又扭了一下子說:
“我不做啦!小姐,這個月的工錢還沒有給我!”
我聽明白了,想辭工不幹,但是,這裡只剩下爸爸一個老人,他是離不開下人服侍的,於是,我振作了一下說:
“阿蘭,你現在不能走!”
“我不做啦!”阿蘭恐懼地了那幢房子,“大小姐死得好怕人,我不做啦!”
“阿蘭,你一定要做,現在只有老爺一個人了,工作很簡單,你好好做,我加你工錢!”
好不容易,我總算又把阿蘭安住了。看著提著小包袱走回下房裡,我鬆了一口氣。沿著院子裡的水泥路,我拖著滯重的腳步,走向客廳。當我推開客廳的玻璃門,迎面而來的,是一種又空又冷的沉寂,大廳裡寂寂無聲,爸爸依然像個塑像一樣坐在那兒。我停住,巡視著這幢房子,這裡面曾經滿了人,曾經充滿了笑語喧譁,我似乎還能聽到夢萍在這兒聽熱門音樂,爾傑在按著車鈴,如萍彎著腰弄小蓓蓓,還有雪姨在那兒笑……短短的半年之間,這裡的人走的走了,死的死了,只留下一個孤單的老爸爸,我呆立著,腦中昏昏濛濛,眼前迷迷茫茫,四周的白牆都在我眼前旋轉,似乎有幾百個龐大的聲音在我邊震盪,我思甩頭,想清楚耳邊的聲音,於是,那衝擊迴盪的各種雜聲匯合爲一個,一個森冷而沉的響聲:
“是你!陸依萍!是你造的!”
頓時間,我覺得背脊發麻,額上冷汗涔涔了。
一陣低沉哀傷的“嗚嗚”聲從我腳下響起,同時,一個冰冷
的東西著了我的腳,我吃了一驚,低下頭,我看到如萍那隻心的小哈狗——蓓蓓,正在我腳下無主地繞著,難道它也知道它失去了它的主人?
我鎮定了自己,走到爸爸邊,輕輕地在他旁邊坐了下來。我無法和爸爸說話,我也無法把自己從那森冷的指責聲中解出來。室,蓓蓓到嗔著,哀鳴不已,更增加了幾分森沉重的氣氛。爸爸了一下,我立刻轉過頭去求助似的對他說:
“爸爸!”
爸爸凝視著我,他的眼凌厲而哀傷,他低沉地問:
“爲什麼要死?”
我不能回答。爸爸冷冷地說了:
“依萍,你該負責任,你搶走了書桓!”
“我是不得已!”我掙扎地說。
“後來是不得已,一開始不是!”爸爸說,“你第一次見書桓,就搶足瞭如萍的風頭,你是有意的!我看你看得很清楚,就像看我自己!”他把手在我肩膀上,他的手抖得那麼厲害,使我的子也跟著不已。他的眼睛地凝視著我。喑啞而肯定地說:“你像我,依萍,你和我一樣壞!”他了我的肩膀,了一口氣。“可是,我喜歡你,只有你一個,十足是我的兒!但是,你不用解釋,我知道得很清楚,你恨我!你一直恨我!無論我怎麼待你,你還是恨我!你恨我這邊所有的人!”
我張開,想加以辯白,但爸爸抓住我肩膀的手突然失去了力量,然後,他的就像一個泄了氣的球一樣癱了下去。我驚跳起來,爸爸已經倒在沙發裡了,他的上半掛在沙發的扶手上,下半拖在地下,臉向下地匍匐著。我抓住他的手,搖著,著:
猜你喜歡
-
完結588 章

虐完我,總裁追妻不要臉
【虐戀深情】一場逼婚,三年婚姻,她不過是個活死人的替身。 真相暴露,林清婉心如死灰,一場車禍后,墨震霆看清內心,原來他愛的一直都是妻子。 虐妻一時爽,追妻火葬場。 他還能否抱得美人歸? “墨總裁保重……”
53.9萬字8 288634 -
連載19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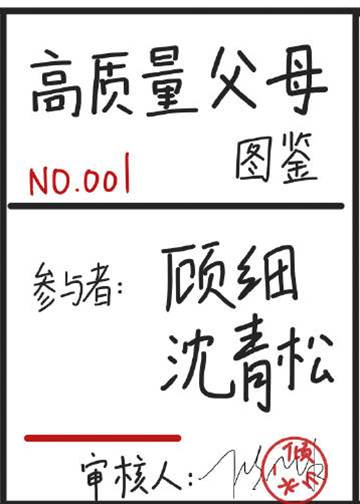
高質量父母圖鑒[快穿]
與其雞娃,不如雞自己!作為快穿局第一對拿到父母資格證的夫妻,顧細和沈青深有感悟:“我們的目標是——成為人類高質量父母!”那些被拋棄、被放棄的孩子,如果有不一樣的父母,是否會有不同的人生………
151.7萬字8 1199 -
完結125 章

信不信我收了你
作品簡介(文案): 京都最近新聞很多。 號外一:聽說陳市長家那個被拐賣的小女兒找回來了,據說被賣到了深山溝裡,過的可苦了。 號外二:聽說陳市長家的小女兒是個傻的,天天說自己能看見鬼。 號外三:聽說陳市長家的小女兒強吻了樓部長家的三公子。(眾人驚恐臉:樓銘都敢惹!!) 陳魚把樓銘按在沙發裡親了好一陣。 陳魚問道:“感覺好點沒?” 樓銘瞇起眼:“丫頭,別逼我動心。” 陳魚懵逼臉———我只是在救人。 會抓鬼的小仙女VS溫柔腹黑病嬌大叔(大約) 其他作品: 《小藥包》、《重生在民政局門口》
44.9萬字8.09 11371 -
連載11 章

鍵盤俠的霸總老公
現實生活中的蘇明月: 膽小懦弱,被人欺負隻會哭嚶嚶。 網絡世界裏的蘇明月: 俠之大者,憂國憂民。給我一個鍵盤,我能毀滅整個地球!手速跟不上大腦的渣渣全部死開,你們、不配、跟我對噴! 國民老公微博下的蘇明月: 我願做雪崩時的第一片雪花、冰雹中的保齡球、海嘯時的滔天巨浪,搞、死、他! 作為一名戰鬥力爆表的鍵盤俠,她的生活平淡又精彩。 直到有天,
2.9萬字8 298 -
完結71 章
誰能憑愛意將月亮私有
陸苗八歲那年,隨父母來到醫院。父親的車撞了人,那男孩沒了條腿。大人告訴她:“你以後多了一個哥哥。”這個和陸苗一起長大的哥哥,名叫江皓月。皓月,擁有著皎皎清輝,光明無限。陸苗一直覺得,這樣比喻江皓月十分貼切。
15.6萬字8 3277 -
完結49 章

好幸運,遇見你!
何其有幸,遇見你!讓我明白,其實幸福只是這麼簡單而已!
14.1萬字8 807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